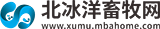这是一支成立21年的乐队。2002年至今,他们的名字几经更改。从“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”“打工青年艺术团”,到“新工人艺术团”“新工人乐团”,再到如今的“谷仓乐队”。他们用音乐表达自我,也用音乐治愈他人。
他们不仅是乐队,更是“音乐社会工作者”。在音乐创作之外,他们兴办打工子弟学校、创办年轻打工者职业培训班,在全国各地乡村进行巡演、与38个村寨共创村歌。
他们行走在中国大地上,演出、倾听、创作、歌唱。他们用朴素、真挚的歌声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无数普通人互相滋养、治愈。这是一群音乐社会工作者的21年跋涉。
 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在乡村里
为村民创作歌唱接地气的“田野之歌”
金色夕阳隐入山峦,湛蓝天空逐渐变得深邃。石头基底、土黄色砖墙、斜坡屋顶,“谷仓音乐厅livehouse”灯牌亮起,附近居民开着汽车、三轮车驶进公社,走进厅内。
在北京市平谷区同心音乐公社内,谷仓乐队正在演出。这是一支有着21年历史的乐队。团队成员曾是老师、小镇青年、矿工,后来成为“北漂”一员。他们以前为城市打工青年歌唱,如今走向乡村,为乡村歌唱、创作。
舞台上,鼓手、吉他手、贝司手就位,厚重的鼓声响起,主唱许多用低沉的嗓音唱起原创歌曲《吾乡》。结尾处,他用家乡浙江海宁方言唱道:“吾在江南向北望,侬在梦里翻红浪,今朝桃花又开放,平谷无恙好生长。”
台下观众大多是平谷当地中老年居民,平时很少观看摇滚或民谣现场演出。即使没有完全听懂歌词内容,但大家的情绪还是被旋律感染了。演出到中途,原本端坐的阿姨们站起身来,随着音乐节奏挥手、鼓掌。
55岁的朱阿姨感觉“回到了年轻的时候”,她鼓动72岁的王大爷拿着葫芦丝和小音响上台,吹奏一首《酒醉的蝴蝶》。王大爷的演奏与乐队风格迥异,但二者在这场乡村音乐会中奇妙融合。正像乐队过去和现在的无数次演出一样,他们在工地与工友共同欢呼,在村庄与老中青三代互动创作。
同心音乐公社的活动正在进行时,团队的另一位主要成员孙恒则带队在重庆兴顺村走访调研,听村里的退休教师、乡贤、老革命、老党员讲述个人故事、村庄历史,与村民共创村歌。
拜访途中,一位88岁的老人拿出了保存完好的薅草锣鼓——一种集体劳动生产时会用到的传统民间乐器。锣鼓声一响,附近居民都围拢来。老人和村民脸上都露出笑容,孙恒内心也感到震撼。“这是从咱们大地里长出的音乐,我觉得特别接地气,这种音乐直击人心。”
“目前歌词创作还没有完成,后续我们可能会在曲调中结合这些本地的音乐元素进行创作。”孙恒说,每到一个地方,村歌的创作都尽量跟当地音乐元素结合。既要传承传统,也要创新,同时要照顾到老中青三代村民的需要。
在工地上
在工棚中播种“打工者之歌”
“谷仓乐队”最初成立时名叫“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”,后来曾更改名为“打工青年艺术团”“新工人艺术团”“新工人乐团”。那时,他们主要在城市的工地上为工友歌唱。
为工友演出的种子是某年冬天在天津一处工棚演出时埋下的。那时,孙恒在打工子弟学校做志愿者,认识了一些学生、家长。他第一次走进工棚为工友们唱歌,天气寒冷,工棚没有任何取暖设施,味道难闻,但大家像过年一样热闹。工友也加入孙恒的演唱,用方言唱起民歌。
后来,孙恒、许多等人组建演出队,创作打工歌曲,常常跑到工地演出。一个夏天傍晚,团队来到某处学校工地。没有专业设备,他们拿着钢筋棍往地上一插,把话筒一捆,就开始唱歌。工友们刚刚下工,端着饭缸子,坐在砖头上,放下安全帽,最初只是拘谨地听着,后来开始“用力拍巴掌”,逐渐在音乐中松弛下来。
音乐创作、演出之外,他们也进行了大量与工人相关的社会实践。2004年,团队机缘巧合发行专辑《天下打工是一家》。后来,他们用赚得的七万多元版税在朝阳区皮村创办打工子弟学校,招募志愿者做老师。2010年,团队在平谷兴办“同心创业培训中心”——实际接近于年轻打工者职业培训班,为大家提升计算机等职业技能。
在巡演中
治愈他人也疗愈自己
2017年,团队开始在全国进行乡村音乐会巡演,工作重心逐渐从城市转向农村。连续三年,团队每年都会进行大约1个月的巡演。陕西、山西、山东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四川、贵州……他们的足迹遍布中国大江南北。在近4万里行程中,他们沿途举办大地民谣音乐会义演50多场,直接参与观众超过3万人。
让团队成员路亮至今印象深刻的演出是在河南老井村。演出结束,他在院子里遇到了一位留守女孩,父母去世,叔叔婶婶在外打工,她跟着爷爷留在老家。他想到了自己远在山东老家的孩子。
路亮常常想起对孩子的亏欠。2016年,他刚到北京不久,妻子和孩子来看望他,分别前去肯德基吃了饭。他借口上洗手间离开,原本一声不吭的孩子突然从餐厅冲到门外:“爸爸,你跟我一起回家。你不要走!”
巡演结束不久,他创作了《孩子》。“这首歌送给那些留守孩子,也是送给自己。我们大多数人,为了理想和生活在外面打工。希望这首歌,能够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陪伴,也是一种疗愈。”路亮说。
在创作中
将心凝聚与38个村共创村歌
乡村巡演途中的见闻触动了孙恒,他萌发了村歌计划的想法。孙恒记得,在四川一个村子,他们邀请村里一位70多岁的老人拉二胡加入演出。那位老人已经40年没有拉二胡了,当他从屋里拿出那把满是灰尘的二胡,丝弦声重新响起,村民都聚拢来,老人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“相对城市而言,乡村的精神文化生活、公共文化活动是比较匮乏的。国家实行乡村振兴其中一点就是文化振兴。我们想通过村歌把老百姓的心凝聚起来,激发老百姓对村庄的热爱。”孙恒说。
目前,团队已经与全国38个村庄共创村歌。提起这项计划,孙恒、许多都对团队在鄂尔多斯木凯淖尔镇的村歌创作印象深刻。他们先后在当地14个村庄与村民共同创作村歌。
“乌兰吉林好地方,西靠滩来东靠梁。刨开黄土挖水库,蓝天白云绿草场。土打墙来盖新房,亲朋好友来帮忙。大锅炖肉小锅茶,边吃边喝边叨啦。茄子开花颠倒颠,老人是咱一层天。马兰开花在路边,村里回来了小青年。西蒙特牛排成行,阿白山羊都养上。春耕秋收不用人,一社五部幸福村。”这是团队与乌兰吉林村村民共同创作的村歌,村歌的治愈力正是源于与村民集体共创的工作方法。
许多说,歌词的前三句源于村民对村庄历史的回忆,以及对村庄自然环境、风俗的描写。“叨啦”则是当地方言,意为聊天、唠嗑。第五、六句通过比兴的手法,前半句用村庄俗语描写自然风物,后半句则表现了村里的某种文化特征,“老人是咱一层天”表达了对老人的尊重,“村里回来了小青年”则隐含着一则故事——一户村民的儿子回村做起了养殖业。
“村民们从没想过自己会写歌创作,当他们真的把一首歌写出来,并且融入自己的生活情感,心里就像乐开了花,特别痛快。这确实对他们自身是一种疗愈。”许多说。
村歌不仅记录了村庄的自然风貌、历史变革、传统习俗,还捕捉了村庄当下的变化。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福建四坪村。在共创村歌过程中,他们请老人参加工作坊,拾起十多年没唱过的地方戏(平讲戏)。村歌创作完成后,本来被搁置了的当地剧团又建了起来,还有年轻人回乡成立传习所。
规划
希望推动百个村庄进行村歌共创
二十一年来,乐队名字几经变化。不断更改的称呼反映了劳动群体的变化,也折射出团队在音乐创作和社会实践上的尝试、突破、改变。
许多回忆,2002年,团队成立之初只有3人,取名为“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”。随着人员逐渐增多,他们改名叫“打工青年艺术团”。作为“北漂”一员的许多、孙恒等人,恰逢城市化、工业化浪潮,怀抱着音乐梦想的他们在工地、工厂为工友歌唱,也逐渐关注到周围工友的故事,尝试用音乐做表达。2009年,团队改名为“新工人艺术团”,后来又改名为“新工人乐团”。
“当时我们觉得这个群体的方向是成为时代的新工人,不满足于普通的生存状态,希望城市给这个群体更多的支持。”许多说,团队名字的变化代表了打工群体的变化,也折射出团队在音乐创作和社会实践上的尝试、突破、改变。2022年,团队改名为“谷仓乐队”,寓意为乡村生产有机的精神食粮。他们不仅是“乐队”,更是“音乐社会工作者”。许多说:“我们希望通过音乐等艺术形式触及一些社会问题,试图改变一些现状。”
“处于困境中的人尤其需要精神上的动力。音乐可以带给人勇气、信心、力量、温暖。”孙恒把过往二十一年的音乐创作和社会实践粗略划分为两个阶段,第一阶段,在城市化、工业化浪潮中,到工地、工厂唱歌,兴办打工子弟学校、打工者职业培训班;第二阶段,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乡村,创办同心音乐公社,进行乡村巡演,协助村寨进行村歌创作。
孙恒说:“我们能坚持21年去做这件事,原动力一定是来自内心深处。无论是以前在工地给工友唱歌,还是现在到乡村唱歌,我的内心都在不断丰富成长,这是一个双向滋养的过程。”
路亮也把在乡村的演出理解为一个互补的过程。“我觉得能到乡村演出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。我们想表达的东西可以传递到更多地方,乡村也需要精神文化生活。我们在演唱也在倾听,我们也把村庄的特色用我们的形式记录下来。”
“在乡村巡演、与村民共同创作村歌的过程中感受到了祖国大地的辽阔、民族文化的多元和丰富。”许多回忆起此前在贵州侗族村寨演出时,当地有句俗语“饭养身歌养心”,当地村民的生活也有大量自发的音乐歌唱。“一个人在生活中可能被挤压得都佝偻着背了,在音乐中站起来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,堂堂正正去发出自己的声音。这是让一个人站起来的过程,也是以歌养心。”
“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,无论是为工友还是为村民歌唱,我们为劳动者歌唱的初心不曾改变。”许多说。
孙恒期待着把同心音乐公社作为原创音乐人聚集地,吸引更多人参与到乡村建设中,用音乐的方式助力乡村振兴。未来3至5年,他希望推动100个村庄进行村歌创作,也希望把集体创作的工作方法传递给更多人。
本版文/本报记者 陈静
统筹/林艳 张彬 (来源:北京青年报)
标签: